当著名诗人桑恒昌将自己新书的名字定为《那一大滴泪水落下来,湿了人间》(济南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我们便已触摸到这部诗集的情感温度。当代诗坛的常青树桑恒昌先生的这部精选诗集,如同一个情感的交汇点,将诗人几十年创作生涯中最具感染力、最适合朗诵的作品汇聚一堂。济南出版社的这一出版策划,可谓独具慧眼,因为桑恒昌的诗歌,从来都不是书斋里的文字游戏,而是注定要被声音唤醒,在空气中振动,直抵人心的艺术佳作。翻阅这本诗集,我们仿佛能听到来自黄河源头哗哗流淌的水声,感受到父母皱纹里的饱经沧桑的岁月风霜,瞥见故乡老屋门前徘徊的略显佝偻的身影。桑恒昌的诗歌世界丰富而又深邃,但其中最动人的,莫过于他对土地、对亲人、对生命本身的深沉眷恋与深刻、深情叩问。

黄河,流淌在血脉中的文化基因
这部诗集开篇就是被广泛朗诵的桑恒昌代表之作《攥着我的半个祖国》,在诗中他写道:“在黄河入海口/捧起一捧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这种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象征直接相连的笔法,典型地体现了桑恒昌诗歌的宏大叙事能力。但他笔下的黄河,从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河流,而是“一道流体长城”,是“将掺着母血的乳/高高举起”的生命源泉。桑恒昌对黄河的书写,超越了寻常的赞美诗模式,而是以一种近乎血缘亲情的方式切入。
在《黄河的思索》一诗中,他直言:“我们说黄河/就是说我们自己/黄河的每一处伤口/都有我们的鲜血横流”。这种认同感,让他的黄河诗篇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现实的切肤之痛。当这样的诗句被朗诵出来,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黄河水的重量,砸在听众的心上。更为难得的是,桑恒昌能够将这种宏大的民族叙事转化为具体的个人体验。
在《船行黄河入海口》中,他描绘了“有岸之河/顿成无涯之水”的壮阔景象,却在结尾处轻轻一转:“云开处/太阳赶来/准备/剪彩”。这种举重若轻的处理,使得他的诗歌既适合大型朗诵会的磅礴氛围,也适合小范围读书会的细细品味。
亲情,永不愈合的情感伤口
如果说黄河是桑恒昌诗歌的筋骨,那么亲情则是其血肉。在这本新诗集中,关于父亲、母亲、妻子的诗作占据了极大比重,而且几乎篇篇催人泪下。
《致父亲》中的父亲形象,是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缩影:“额上的风雨装订成册/阳光迷得您老泪纵横/双手把犁杖磨成拐杖”。桑恒昌捕捉细节的能力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不过多渲染情感,而是通过具象的描写,让情感自然流淌。这样的诗句在朗诵时,不需要夸张的语调,平实的诉说反而更能触动人心。
而对母亲的怀念,更是桑恒昌诗歌中最锋利也最温柔的部分。《中秋月》只有短短五行:“自从母亲别我永去/我便不再看它一眼/深怕那一大滴泪水/落/下/来/湿了人间”。这首诗的朗诵效果极为震撼,当朗诵者缓缓吐出最后一个字,那种克制的悲伤往往能让全场寂静无声。
桑恒昌的亲情诗之所以适合朗诵,在于他找到了一种普遍性的情感表达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每个人都有无法弥补的遗憾,当他在《跪别祖坟》中写道:“双膝跪出了坑/泪水淹透了心”,他道出的是人类共通的哀伤。这种普遍性,使得他的诗歌能够跨越个体的差异,直击每个听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故乡,灵魂最后的栖息地
桑恒昌的故乡情结,在他的诗歌中表现为一种复杂的张力,既渴望回归,又明白真正的故乡已经只能在记忆中寻找。
《我的家园》中的诗句:“我和母亲/隔的是/一条剪断了的脐带/我和家园/隔的是/一层切了又切的皮肤”,生动地表现了这种离散感。
在《液体的故乡》中,他将这种情感提升到了更高的层面:“黄河长江/是我/液体的故乡”。这种将具体地理转化为精神符号的能力,使得他的乡愁诗避免陷入沉溺个人伤感的窠臼,而具有了更广阔的意义空间。
特别值得一提的,也是许多人在各种场合朗诵的那首催人泪下《旧时燕子》。在这首诗中,诗人通过燕子的意象,将时光流逝、物是人非的感慨表达得淋漓尽致:“旧宅里半栋老屋还在/老屋里半个泥巢还在/泥巢里我的目光还在/母亲啊,你何时飞来”。这样的诗句在朗诵时,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回环往复的韵律感,仿佛燕子年复一年的迁徙,暗合了诗人对故乡永恒的追寻。
生命,在疼痛中觉醒的存在感
桑恒昌的诗歌不仅有情感的温度,还有思想的深度。他对生命的思考,尤其体现在面对疾病、死亡的主题上。
《这个夏天从冬季里度过》一诗是写给病中妻子的。诗句中饱含的无力之感与不懈坚守令人动容:“一个偏瘫的妻子/我扶着走/一个全瘫的妻子/我背着走/一个植物人的妻子/我抱着走”。这种近乎残酷的写实,反而折射出爱情最本质的样子——不是风花雪月的浪漫,而是不离不弃的陪伴。
在《深夜大雪》中,他写道:“几度生死/种进文字里/拼着所有气息/去闯明天的际遇”。这种面对生命无常的勇气,正是桑恒昌诗歌的精神内核。当这样的诗句被朗诵出来,它们传递的不仅是美感,更是一种生命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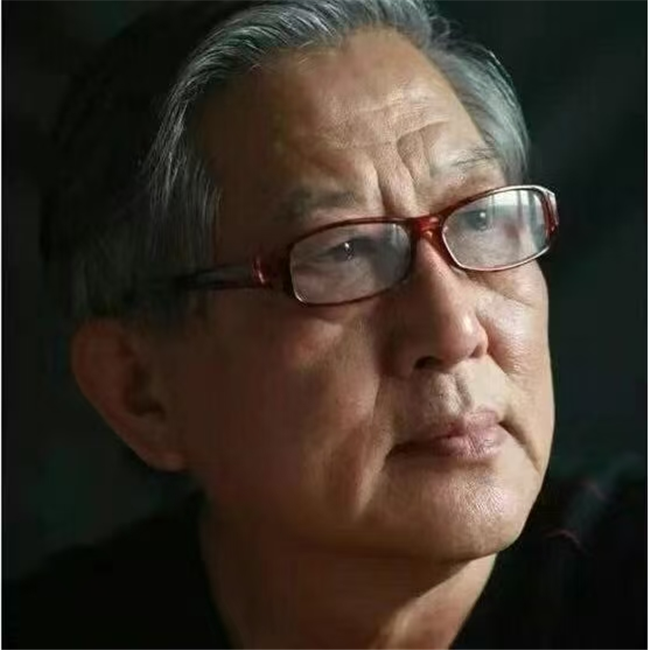
朗诵,诗歌的第二次生命
这本诗集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精选的是“最适合朗诵的诗作”。桑恒昌的诗歌之所以容易被朗诵且效果显著,我以为主要源于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语言上,他避免生僻词汇和复杂句式,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最深沉的情感。在《筷子》,他写道:“每当饱餐已毕/它才有片刻的喘息/来不及洗一洗周身的辛劳/只是默默地看着你”。这样平实如话的诗句,在朗诵时几乎不需要任何解释,就能直抵人心。
节奏上,他的诗歌具有内在的音乐性。如《黄河》一诗中的诗句:“从小溪走来/向大海走去/披一身落日的霞光/穿越八千里云雨”,长短句交错,形成自然的呼吸节奏,非常适合朗诵时的语气处理。
意象上,他善于运用具象而富有张力的意象群。黄河、故乡、父母、老屋,这些意象既是具体的,又是象征的,能够在听众脑海中迅速唤起共鸣。
更重要的是,桑恒昌的诗歌始终保持着情感的真挚与思想的锐利。他不回避痛苦,不粉饰现实,而是以一种近乎固执的真诚,面对生活的全部真相。正是这种真诚,使得他的诗歌在被声音传递时,能够产生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那一大滴泪水落下来,湿了人间》这个书名本身,就是一首微型的诗。它告诉我们,诗人的使命不是逃避人间,而是用泪水浸润人间,是用诗歌照亮人间。
桑恒昌的这部诗集,仿佛一个情感的共鸣箱,将个人的悲欢离合放大为时代的集体记忆。当我们朗诵这些诗歌时,我们不仅是在欣赏文字的艺术,更是在参与一种情感的仪式。桑恒昌用他的诗句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共同怀念远去的亲人,共同思念遥远的故乡,共同思考生命的意义。这或许正是诗歌最珍贵的功能:它不是逃避现实的象牙塔,而是帮助我们更深刻、更真诚地面对现实的桥梁和媒介。
桑恒昌的诗歌之所以能够“雅俗共赏,老少争诵”,根本原因在于他触及了人类永恒的情感核心。在他的诗世界里,黄河的涛声与母亲的叮咛交织在一起,故乡的泥土与生命的追问相互叩击。这些诗歌经过朗诵者的二次创作,获得了一种超越文字的生命力,它们不再只是纸上的符号,而变成了空气中的同频共振,心灵中的共鸣回响。
《那一大滴泪水落下来,湿了人间》不仅仅是一部诗集,更是一部声音的档案,它记录了一个诗人如何用他最真诚的方式,爱着这个充满泪水和希望的人间。当这些诗歌被一次次朗诵,被一次次传播,那一大滴泪水便真的落了下来,湿润了每一个聆听者的心田。在这个意义上,桑恒昌的诗歌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成为我们共同的情感遗产,持续地温暖着这个有时过于寒冷的人间。(宋俊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