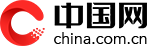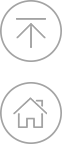“为己之学”是朱子理学的重要宗旨,朱熹曾说:“今须先正路头,明辨为己为人之别,直见得透,却旋下工夫,则思虑自通,知识自明,践履自正。”确定为己的方向对为学有开辟源头、校正路径的作用。为己之学的出发点与作用对象都是“自家身己”,所以朱熹说:“须于自家身己上理会,方是实学问”,又主张“自做工夫”。
朱熹对自家、身己等概念的集中论述是少见的,这与为己之学的实践特征有关,朱熹说:“明道先生言介甫说塔,不是上塔。如今人正是说塔,须是要直上那顶上去始得,说得济甚事?”为己之学在朱子学中是一个“实做工夫”的问题,需要学者通过自己具体努力来实现。因此对自家概念的集中阐述可能会使为己之学成为又一层议论,最终无益于学者身心。但是朱熹在他的著作、书信和讲论当中广泛地提到“身”“身己”“自家”“己”等概念,这说明朱熹对“自家”问题始终保持着自觉。如果将“为己之学”看作是学者实现理想人格、使天理转化为具体的现实人格的过程,那么在“己”范围内的“自家”“身己”等结构就是天理转化的场所。虽然朱熹的“为己之学”观念已经得到重视,有学者说明了“为己”与“成物”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并且是否“为己”可以被看作是否“正学”的标志,但学界对“己”概念的讨论仍不多见。明确“真己”才能准确了解“为己”,这篇论文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讨论“自家”概念,以期为朱熹理学思想中形上天理转化为现实人性的必要结构提供一个简单融贯的说明。
一、“自家”的涵义
明确“自家”在朱熹理学中的具体涵义是讨论它的基础。“自家”并不与形而上的理学范畴如“理”“性”完全对应,也与现代哲学中的“身体”“自身”以及“主体”等概念不相应,而更多地表示现在常见的反身代词“自己”的含义。朱熹有时将“自家”与“身己”“躯壳”等概念合用,表示“自家”也有为己所有、亲身所感、亲自行为等方面涵义。下面举出几个例子:
1.今学者皆是就册子上钻,却不就本原处理会,只成讲论文字,与自家身心都无干涉。
2.而今读《大学》须是句句就自家身上看过。
3.存心不是纸上写底,且体认自家心是何物。
4.如一个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却寻得一线路与自家私意合,便称是道理。
5.若自家曾实做工夫,如忍痛然,我自痛且忍不暇,何暇管他人事?
6.观书不可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余。
7.盖心便能把捉自家,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
8.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义利公私,分别得明,将自家日用底与他勘验,须渐渐有见处,前头渐渐开阔。
9.大抵人心流滥四溢,何所定止?一日十二时中有几时在躯壳内?与其四散闲走无所归着,何不收拾令在腔子里?
由1可以看到,“自家身心”强调自己的身心,类似于第2条“自家身上”。但2中的“身”与二气五行、众窍百骸的物质性的身体有所区别,不能将此句解为“在自己的身体上看过”而是要用《大学》的义理来参照、调整自己。第3条中“体认自家心”则是在体认自己的心,而“心”在朱熹理学中,既指作为“心统性情”的功能,也作为“人心”“道心”的有内容的意识的对象,所以这里的“自家心”可以看做是作为体认对象的自己的意识状况。
从这三条引文来看,“自家”在朱熹理学中与“身”“心”合用,作为对“自己”的指称,表示“自己”的身、心。在这种表示中,“自家”的出现标志了身、心从行动的主体转为行动(体认、看、相干涉)的对象。
第4、5、6条表明自家包括私意,力量、感受等内容,这些被包含在“自家”之中,与上面所提到的自家“身”“心”有着略微的不同,上面的“自家身心”以“自家”是将行动的主体(身、心)看作客体的指示,而这里则是把体认到的内容(力量、私意、痛)包含在“自家”中,将“自家”看作一种展现在意识中的内容。“忍痛然”是一种感受,朱熹强调做工夫要如忍痛,当然不是指感官感觉而言,而是要对做工夫过程中的主体状态有深切的感受。“自家力量”则是指认识能力,这既包含读书中读者的经验、学识,也可以是精神状态和技巧,这些都可以被归为认识的“力量”,常使“自家力量有余”,这是达到认识的“洒落融释”的条件。“自家私意”是自家独有的愿欲所见,这种所见会继续影响后来的认识,使人将非道理的认作是道理。从朱子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感受都是由心主宰的,但又都归属并展现在“自家”之中。
第7条强调“自家“无法把捉心,心却能决定”自家“。这说明“自家”受心的作用所决定。这里的“自家”应指包含着私意、力量、对身心的感受等,是属于“情”层面的事物,能够被心决定。第8条中,学者要“将自家日用底与他勘验”,也就是说作为“自家”“日用底”内容可以由为学得到改变。第9条则提出了另一个现象,心有时不在“躯壳”中,走作到别处,所以需要人刻意收拾。也就是说,人的认识能力不一定集中在指代自己的“自家”“躯壳”上,而这时作为意识对象的“自家”也会陷入停滞。这进一步说明了认识能力对“自家”的决定作用,同时也表示出“自家”具有可连续性的性质。
通过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到朱熹使用的“自家”概念:首先作为指代自己的代称;其次由自我指代进一步,作为在反思中体现出的,包含着感受、经验、好恶的意识现象;并且“自家”是由心之知觉所决定的,属“情”的意识现象;最后,“自家”受心的知觉运用的影响,其内容有时会被忽视而陷入停滞,有时则被知觉所改变。
这样对“自家”概念的总结,使“自家”成为了一种属“情”层面的意识现象。虽然日常生活中认为现实中的自我与自我所面对的事物都是实存的,但是在朱熹理学中,现实的人与事物本质上是气依照理流行的过程,知觉也是如此,朱熹说:“是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自家”并非人所禀受的性,因为性并不直接显示自身,而是作为情的基本原理被了解,“自家”也不是作为主宰与知觉的心,因为心是气化流行的结果,是兼括体用的总体。“自家”是心运动变化发出的现象,既不穷尽“心”的内涵,也不能决定心的活动,但却作为心反思的场所支持着“心”功能的展开。
二、“自家”的结构
作为单纯指“自己”的“自家”是人心知觉功能在反思中的体现。朱熹说:“盖寂然常感者,心之本体。惟其操舍之不常,故其出入之无止耳。惟其常操而存,则动无不善,而瞬息顷刻之间,亦无不在也。颜子三月不违,其余则日月至焉,以此心之常感而易危之故也。”心的基本状态是常常有感,其知觉功能是时时刻刻起作用的。知觉功能是人心活动的基础,是能知觉,而心具体的思虑认识的内容则是所知觉。只要心仍存在,能知觉就不会停止,这就是“寂然常感”的“心之本体”。
虽然心的认识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人心本身是一,其知觉是唯一而持续的。朱熹说:“人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所以为知觉者不同。”心所知觉的内容则随着知觉能力的转变而发生变化,有集中于形气与集中于性命之别。对心的知觉不加以提撕,心的内容就会有偏离天理的危险。虽然所以为知觉者不同,但是能知觉者未尝不同,能知觉者有责任发挥自身功能以完善知觉,所知觉也因为属于相同的能知觉而具有统一性。朱熹说:“且自体认自家心是甚物?自家既不曾识得个心,而今都说未得。才识得,不须操而自存,如水火相济自不相离。”“体认自家心”是以心识心,也就是在反思心的知觉能力本身。心的知觉能力伴随着全部知觉,在进行知觉时加以反思,心的能知觉也就现成地成为可以被知觉的“自家心”。而被体认到的知觉能力作为“自家心”,在现象上又成为了体认者。也就是说,虽然实际上是心进行了认识体验的活动,但人在主观上体验为“自家”认识了事物。因而“自家”这一表象内又可以包含各种被人体验到的内容,并且将这些内容都看作属于“自家”的。单纯指代“自己”的“自家”是认识能力反思的产物,同时也具有统合知觉内容的作用,也就是一种在现象上将所认识的内容统一于自我表象之下的能力,是“不须操而自存”的基础。
作为自己的“自家”贯穿着反思下的众多知觉内容,“自家”的基本组成是心的知觉功能的现象,被认识的事物被表示为“由自家认识的事物”“包含在自家内的事物”,表现出事物属己的现象。自家内可以包含念虑、情感、意志、知识等多种内容,对理的体认也在其中,并由“自家”得到扩展。
人对理的认识被朱熹称作“源头”或“本领”,在面对外在的客观事物时,“源头”与事物发生联系,才能在向内与向外两个方面产生良好的结果。朱熹说:
要知这源头是什么,只在身己上看,许多道理尽是自家固有底。仁义礼智,‘皆知广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这个是源头,见得这个了方可讲学,方可看圣贤说话。恰如人知得合当行,只假借圣贤言语作引路一般。
“只在身己上看,许多道理尽是自家固有底”就是源头,是对“自家”中包含着对理的体认这一现象的肯定。这个源头是对理的知觉,有了已知之理,圣贤言语、师友讲学中的义理才能被纳入到源头中,人才能依照认识的理而行动。朱熹说:“凡事事物物各有一个道理,若能穷得理,则施之事物,莫不各当其位。如‘人君止于仁,人臣止于敬’之类,各有一至极道理。”就事物来看,一事物之为事物,必然有其所以然之理,这个理是具体的实理,是天理的部分内容。万物虽然各有一个道理,但万物之理是同一理,万物在同一理之中各有其位置。因此已知之理与事物之理潜在地可以贯通,顺着已知之理,事物之理可以逐渐被归入源头。朱熹说:
这个事须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齐贯穿在这里,一齐理会过。其操存践履处固是紧要,不可间断。至于道理之大原固要理会,纤细委屈处也要理会,制度文为处也要理会,古今治乱处也要理会,精粗大小无不理会。四边一齐合起,工夫无些罅漏。东边见不得,西边须见得;这下见不得,那下须见得。既见得一处,则其他处亦可类推。而今只是从一处去攻击他,又不曾着力,济得甚事!如坐定一个地头,而他支脚也须分布摆阵。如大军厮杀相似,大军在此坐以镇之,游军依旧去别处邀截,须如此做工夫方得。
理会道理应该上下四方大小精粗一齐理会到。在具体理会的过程中则是见得一处而由此类推。作为对天理的部分体认的源头,通过作为自己的“自家”对知觉到的不同内容的联系,使得对天理整体的体认可以由一事物转到另一事物,就一处去认知后再就一处认知,心的知觉从天理这一部分转移到另一部分,从已知觉之理贯通进入未知觉之理。朱熹以大军厮杀为喻,已知之理作为源头,是坐镇的大军,而理会别的理像是出去探寻的游军。游军是大军派出的,正如对新的具体事物之理的体认是建立在已知之理的基础上的,但对事物之理的体认并非是已知之理分割出一部分,而是已知之理在其边际处、“罅漏”处随着“理一”的联接与其他事物之理自然汇合。所以朱熹说:“万理虽只是一理,学者且要去万理中千头万绪都理会,四面凑合来自见得是一理。”通过“理一”,本源在“自家”内得到扩充。
源头扩充的过程中,人对理的认识随着天理内在的自然次序而展开,因而面对事物的时候能够顺应事物之理,将其合理安排以实现事物之应然,实现天理由“自家”而到事物,由“忠”而达到“恕”的过程。源头的扩充可以实现事物的合理化,在人与事物的关系中体现出物我无际的趋势。从源头出发,事物与自我的界限逐渐缩小。《朱子语类》记载:
寿昌问:“鸢飞鱼跃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说禅,这个亦略似禅,试将禅来说看。”寿昌对:“不敢。”曰:“莫是‘云在青天水在瓶’么?”寿昌又不敢对。曰:“不妨试说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既而又曰:“须将《中庸》其余处一一理会令教仔细。到这个田地时,只恁地轻轻拈掇便自然理会得,更无所疑,亦不着问人。”
作为事物的鸢飞鱼跃中有理贯穿流行。所见者是鸢飞鱼跃之所以然的实理,而对这些实理的认识都是自家知觉参与下的实现,事物之所以流行发现都在源头之内,由此可以说“我今正是渠”。自家所有之理正是事物所以然、所当然之理,物与我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分别。到此境界之后,面对事物已不需要主观用力,只是轻轻提起,注意到与其对应的理,就足够正确应对事物。
“自家”中也包含着不合理的成分。这种不合理的成分并非本质上是“无理”的,朱熹说:“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没有知觉之理,则知觉是不可能的,但知觉的内容仍有不反映着特定事物之理的可能。
朱熹承认“自家私意”也属于“自家”,但否认“私意”能够作为“源头”推动人与事物朝向积极方面发展。朱熹说:“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私意”可能反映着一部分的理,但不能顺着客观的理的联系实现内外两方面的合理化与扩充,造成人与事物的间断,导致不良结果。
因此朱熹强调在“源头”扩充的过程中,能知觉的心要时刻起作用,能知觉一旦走作,“源头”就会出现停滞。朱熹说:“公今只看一个身心是自家底,是别人底?是自家底时今才挈转便都是天理,挈不转便都是人欲。要识许多道理是为自家,是为别人?看许多善端是自家本来固有,是如今方从外面强取来附在身上?只恁地便洒然分明。”先要体认事物“是自家底”,并非在具体认识前主张事物“就是自家的”,而是通过对“是自家底”的追问来唤起反思,从而维持知觉能力对身心、道理、善端等多重内容的认识,使得这些认识不陷于静止、局限、琐碎、混乱而趋向准确、联系、广大,知觉持续用力的过程就是“挈转”知觉内容,将它们在“自家”之中加以联系的过程。如果不通过“自家”进行反思,就会造成心的知觉集中于具体事物上,出现“逐物”“放心”“走作”乃至于“四溢流滥”的后果。这种情况下,“身心”“善端”等名目无法与“自家”已有的精神与义理状态加以联系,其义理内容也无法对主体展开,从而成为“别人底”“强取来附在身上”的事物。朱熹说:
要知天之所以与我者,只如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无辞逊之心非人也”。今人非无恻隐、羞恶、是非、辞逊发现处,只是不省察了。若于日用间试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攒出来,就此便操存涵养将去便是下手处。只为从前不省察了,此端才见,又被物欲汩了,所以秉彝不可磨灭处虽在,而终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
四端发现是仁义礼智之性的体现,于四端发现处加以省察才能知觉仁义礼智的内容。在认识之外还要操存涵养,使知觉保持在义理上,如此才能奠定工夫的基础。否则虽然天理之所赋予时时存在,但终究不能恢复其本来面目。省察是要见得此理,而操存涵养则是将知觉集中于理上。知觉集中在理上,才能顺从此理的自然次第,去除主观臆想,进而由“理一”实现源头的扩展。朱熹说:“自见住不得时便是。某怕人说‘我要做这个事情’。见饭便吃,见路便行,只管说‘我要作这事’何益。”理是自然,但是自然之理并不排斥人的知觉认识,持守涵养将知觉时刻集中在自然之理上,人的行为也随着内在于理的客观次第节目而展开,不随意停止,表现出稳定持续的性质,这种知觉也可以称为“道心”。“我要作何事”也是心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以作意而非顺从自然来推动心的知觉,一旦作意消失或者发生改变,人的行为也随之发生改变,源头也就停滞了,这种状态也被称为“人心”。
三、“自家”现象的不可替代性
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家”,在客观上是多数的,但“自家”对每个个体自我都表现为唯一的,对每一个个体都显现为不可替代的自我意识。
每个人所禀赋的气是各自独立的,以禀赋为基础的心的功能也是各自完满的。朱熹说:
“继之者善”,便似日日装添模样;“成之者性”,便恰似造化都无可做了,与造化都不相关相似。到得“成之者性”,就那上流行出来,又依前是“继之者善”。譬如榖,既有个榖子,里面便有米,米又会生出来。如果子皮里便有核,核理便有仁,那仁又会发出来。人物莫不如此。如人方其在胞胎中受那父母之气,则是“继之者善”。及其生出来便自成一个性了,便自会长去,这后又是“继之者善”,只管如此。
“继之者善”是事物之理随着形气流动而逐渐完备,“成之者性”则是形气已具之后理则随之稳定,表现为特定的理。人出生之前虽然日日受父母之气而发育成型,但出生以后自身禀受的理是各自完满的,与他人不相关,正好像造化到此都停止了一样。“自家”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心又是虚灵之气运动的结果,所以每个人的“自家”都是其自身所禀赋之气的结果。
每个人的气与他人的气没有直接关系。朱熹说:“论万物之一源,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万物都以理为依据,而构成万物形质的气有所不同,所以赋予之理相同而禀受之气不同;从万物性质各自不同而言,万物虽然同是由气构成,而万物之为万物的所以然绝不一样;前者可以说是“继之者善”,后者可以说是“成之者性”。虽然每个人的禀赋差异存在,但人都是人的一气产生,此气的总体性质不变,所以人都具有能知觉认识天理的共性。另一方面,人之所以构成自家的理并无不同,都为所有人禀受,但是人所受之气各自不同,所以人是拥有相同功能的各自不同的现实个体。
“自家”是反思的自我意识,人对“自家”的认识可以在对外在事物之前,也可以在体认到事物之后,再将对事物的体认通过反思纳入到“自家”之中,朱熹对门人言:“诸公全靠某不得,须是自去做工夫始得。且如看文字须要此心在上面,若心不在上面,便是不曾看相似,所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只是‘心不在焉’耳。”朱熹鼓励门人自作工夫,不依靠他人。朱熹还说:“读书是自家读书,为学是自家为学,不干别人一钱事,别人助自家不得。”这也是表示相同的意思。每个人的“自家”都是心的作用,其知觉体会的内容对自我而言是直接的,但是他人与事物对自我来说不是直接的,而是处在待知觉的状态。他人的行为与认知无法取代自我的知觉,以他人为对象的知觉实际上仍是“自家”的部分。所以不论读书还是做事,都要“自作工夫”,通过知觉运用将对事物的体认纳入自我意识,才能实现自我完善。作为自我完善的“工夫”“学问”必然由“自家”的改变与发展来实现,在为学与处事中依靠他人,实际上等于取消了个体心的知觉的反思过程。
“自家”是不可替代的自我意识,是责任的承担者。朱熹说:“若不就自家身心理会教分明,只道有些病痛不妨,待有事来旋作安排,少间也把捉得一事了,只是有些子罅缝,少间便是一个祸端。这利害非轻,假饶你尽力极巧,百方去做,若此心有些病根,只是会不好。”“自家”与事物处于“已发”这一逻辑层面而相互作用。“自家”如果不能分明合理,遇到事物就不能依照事物之理应对,从而导致祸患的发生。要使“自家”趋于合理,就要通过为学的过程来充分发挥心的知觉能力。朱熹说:“更有一事,如今学者须是莫把做外面事看。人须要学,不学便欠缺了他底,学时便得个恰好。”人的不学,在朱熹看来等于在最初意义上未尽自己的责任。
四、“自家”在朱熹理学中的意义
综上所述,“自家”是以心的知觉功能为基础进行扩展、在现实过程中走进事物的意识现象。“自家”是理学为学工夫的起点与接受者,实现了朱熹理学中自然与人为的贯通,确保了自然与应然的一致。从理气运行的客观方面而言,“自家”帮助“为己之学”沟通了“诚”与“诚之”,让本质的理气作用贯穿到现实现象中,从而说明了自然与社会发展具有共同秩序,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推动自然与社会整体向前发展。
《中庸章句》解释“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天理是真实无妄的本然,“己”所处的位置正在“诚”与“诚之”之间,将天理的本然转换为现实的应然,以“诚之”的工夫,由未能真实无妄而趋向真实无妄。
万物都同样地禀受天理全体,天理全体本身是真实无妄的,但万事万物就自身禀赋来看,都未能真实无妄。朱熹说:
廖子晦得书来,云“有本原,有学问”。某初晓不得,后来看得他门都是把本原处是别有一块物来模样。圣人教人只是致知、格物,不成真个是有一个物事如一块水银样走来走去那里。这便是禅家说“赤肉团上有一个无位真人”模样。
廖德明认为存在一个事物现实地规定人的行为,而且这种规定也是现实地显现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天理是某种现存事物,那么真实无妄的天理就会与处在同一层面、未能真实无妄的人与事物产生差异,天理只能对万物进行主宰式的约束。这种说法有些宗教色彩,所以朱熹认为廖德明的论述与禅家之说接近。朱熹反对学者把天理当做“有个物事”或者“要先见一个浑沦大底物捺在这里”天理本原处不是一件物事,天理也不支配控制事物。从天理来看,不仅人本然地具备天理,天下万物莫不如此。《朱子语类》记载:“人与万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又载:“人物之生,天赋之以此理,未尝不同,但人物之禀受自有异耳。”人与物都实现了天理的一部分而生,向上就其禀赋而言都是禀赋天理,人与万物并无不同。然而人与万物都不即是天理,而是实现着的部分天理,所以向下就各自禀受而言都有不同。也可以说,“本来已有”对人物来讲并无不同,但人与物之所得以为己有者相差甚远。物之所得并且表现为其性质功用的是具体的、有限的,如蝼蚁有君臣、附子热、大黄寒之类;人之所禀则表现为心能知觉万理、应万事。朱熹说:“动物有血气,故能知。植物虽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见。”这是说动物能知而植物并无知觉功能。知觉与物质性的血气、生意相关,又可以说能知觉是气化的结果。朱熹提到:“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心之气的虚灵特质是人与动物知觉差异的最大原因。“物受天地之偏气,所以禽兽横生,草木头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间有知者,不过只得一路,如鸟之知孝、獭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能耕而已。人则无不知,无不能。”朱熹肯定动物做出的合乎理的行为是伴随着知觉意识的。鸟獭犬牛之类气禀有偏,其能知觉有限,而人的气禀清正纯全,所以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人心的能知觉并不现成地知理,只是体现出可以无所不知,可以无所不能的性质。按照《大学章句》的论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对天理的体认、对万物之理的全知,应对万事的全能是心的能知觉之理的充分发挥的结果,而能够对天理进行体认,是人已经具有的能力。
“自家”依靠现实已有的能知觉体认天理,从而超出人与事物的局限,在更大的范围上实现自然的天理。事物与人都体现天理,但事物与人所体现的都是天理中有限的一部分。天理在草木但草木有生而无知,天理在动物但犬只能守御,牛只能耕作,愚夫愚妇虽然日日履行天理中的部分却不知天理。事物虽然有具体的事物之理,但只要采取特定事物的视角,那么事物蕴含的理就是有限的。人能够实现的理虽然是全面的,但是人在实现自身所能达到的理的过程中受气禀的拘束影响,产生贫富寿夭贤愚之分。事物之理有所局限,事物之间出现矛盾,天理流行于事物的过程就会受到阻碍,就需要人通过完善自身来协调事物。朱熹认为人具有能够知觉全体天理的禀赋,在现实的作为意识的“自家”的扩展过程中,人依照所体认的理的应然来行为,同时也在应对事物的过程中安排事物,使事物在流动运转中超出自身,在更大的范围内具有意义。这就使人的主观思虑营为在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理在事物上的流行,以“诚之”的过程来实现“诚”的自然之理。
通过应然与自然的沟通,朱熹将学的可能性与为学的基本途径都包含在“自家”中。人禀赋是自然的,人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禀赋,实现这一发挥需要对天理加以认识,因此为学是人应该从事的活动。朱熹说:“某不是要教人步步相循都来入这圈套,只是要教人分别是非教明白,是底还他是,不是底还他不是。大家各自着力、各自撑柱,君尽其职,臣效其功,各各行到大路头,自有个归一处。是乃不同之同乃所以为真同也。若乃依阿鹘突、委屈包含、不别是非,要打成一片,定是不可。”在朱熹看来,不同之同乃所以为真同。他人与自己观点或言论相同是次要的,重点在于人应该探索天理。在对天理的认知上,人与人虽然一时观点不能全部相同,但通过为学的过程,最终能够在天理归一的自然基础上取得意见统一,在各司其职的同时实现并力合作。
朱熹对“自家”概念的自觉也使他在对待前辈学者的态度上同样重视主动的精神。朱熹说:“周子、二程说得道理如此,亦是上面诸公那趱将出来。当杨、刘时只是理会文字。到范文正、孙明复、石守道、李太伯、常夷甫诸人,渐渐刊落枝叶,务去理会政事,思学问见于用处。及胡安定处,又教人作“治道斋”,理会政事,渐渐那得近里。所以周、程发明道理出来,非一人之力也。”朱熹认为理学的产生离不开宋初诸公的努力,学术文化的传承积累最终使义理得以发明。这也给出了道学发展的实践原因,即前人在具体事物上以实学的态度发明事物义理,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与实际事物知识的积累下,又由周程诸子知觉前人所得而进一步加以扩充,及至于事事物物相发明,才最终体贴到一贯天理之处。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位学者都付出了亲自努力。学统的传递并非前人传于后人而已,更是后人对前人之学加以研究的结果。学统的传递是自家的主动参与而非对前人的依赖,后人与前人所知觉的理要相同但其言论不必相同,所以朱熹说:“经书中所言只是这一个道理,都重三叠四说在这里,只是许多头面出来。”这使朱熹在思想传承上采取了相对开放的态度,将思想与学术传承看作一个实践的过程,从而为后学多角度地发展朱子学作了理论上的奠基。(《朱子学研究》编委会编:《朱子学研究》第35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