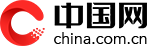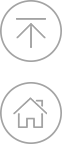摘要:儒家思想曾深刻影响了西方“自由放任主义”的内涵,而其本身在经济上也存在着鲜明的“自由放任”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儒家承认人之自利心的存在,并认可人们积极追求物质财富的行为;二是遵从劳动分工,认为不同分工共同促进社会发展,反对干预人们自然形成的分工;三是反对限制商品流通的任何税收政策,主张发展自由贸易;四是反对政府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主张限制税收进而限制政府开支和规模。这些鲜明的“自由放任”倾向,与强烈的伦理取向,共同构成了儒家经济思想的重要特征。
关键词: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儒家;
引言
重义轻利是儒家的一般形象,以致于人们将古代中国经济发展迟滞、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归咎于儒家经济思想的阻碍。但陈焕章发现儒家在经济政策上不仅赞同“社会立法”,还赞同“自由放任”【1】。唐庆增也认为儒家之财政学说有两大特点:“一曰放任主义”,“二曰薄敛”【2】。“自由放任”是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朱家桢认为用它来概括儒家的“开禁民利”思想并不妥当【3】。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自由放任”的内涵与儒家思想之间的深刻渊源,便会相信用它来阐释儒家经济思想的倾向性并无不妥。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形成,离不开法国重农学派对“自由放任”概念的阐释和鼓吹,重农学派从他们的自然法哲学推衍出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张,而其自然法哲学又与中国儒家的思想传统存在着深刻渊源【4】。并且,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认为,儒家的经书就是自然法典,是中国的基本法,儒家中国就是一个完全按照自然法统治的国家,人们完全按照自然法则进行生产和生活【5】。不言而喻,根据魁奈的观点,信仰自然法并对自然法有着最高水平理解的儒家,在经济思想上必然也是一种“自由放任主义”。古代中国当然不像魁奈描述的那样美好,儒家也不是完全的经济自由主义,但说儒家经济思想中存在“自由放任”的倾向,却无不可。
1912年,陈焕章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第一次使用“自由放任”一语指代儒家社会主义运动遵循事物之“自然发展进程”的特征【6】。1936年,唐庆增在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书中也指出儒家财政学说具有“放任主义”特点,认为儒家的“自由放任主义”就是“藏富于民”,反对官办营业与民争利【7】。陈、唐二氏皆留学美国学习经济学,他们发现儒家经济思想的“自由放任”特征显然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在陈、唐之间,胡适、熊梦也曾用西方的“自由放任主义”分析老子的经济思想【8】。但重农学派对“自由放任”这一概念的阐释与发展,毕竟是受了儒家思想而非老子思想的影响,而且魁奈还将老子与道教混为一谈而进行了严厉的批判【5】。1983年,侯家驹出版《先秦儒家自由经济思想》一书,分别讨论了孔子、孟子、荀子的经济思想及其“自由放任”特征【9】。1992年,谈敏出版《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一书,比较了重农学派和儒家“自由放任”思想的异同【4】。1998年,马涛发表《论儒家的自由经济思想》一文,简单考察了孔子、孟子、叶适、丘浚等儒家人物的自由经济思想【10】。同年,胡寄窗出版《中国经济思想史》【11】,2016年盛洪出版《儒学的经济学解释》【12】,也都提到儒家经济思想的“自由放任”特征。
在这些研究中,陈焕章、侯家驹、马涛等将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经济思想视作儒家“自由放任主义”的典型,似不妥。虽然司马迁在学术上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对人类自利心的认识也与儒家一脉相承,但他说的“善者因之”明显是黄老“因循为用”思想的翻版,是汉初“与民休息”之现实政策的反映。而谈敏将孔子说的“无为而治”视为儒家的“自由放任”思想,本文也不认同。因为孔子所说的“无为而治”是一种领导艺术,指君主“为政以德”,选贤与能,使贤能各敬其职,从而垂拱而治,而不是指经济管理的“自由放任主义”。不仅儒家,老子的“无为”也不是经济自由主义,因为老子之“无为”是要遏绝人欲,根本反对发展经济,遑论成为“自由放任主义”的中国渊源?本文认为上述研究主要有两点贡献:一是指出了儒家“自由放任”主义的自然法基础,即儒家的天道思想;二是指出了儒家“自由放任”主义的一般原则,即孔子所说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研究的不足之处,除了误将儒家的“无为而治”等同于“自由放任主义”,将司马迁的“善者因之”视为儒家“自由放任主义”的代表,主要是缺乏对儒家经济思想之“自由放任”倾向的系统考察。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提出新观点,也不在于发现新材料,而在于努力用旧材料论证一个较少为人们注意的老观点,尽可能全面地去展示儒家经济思想“自由放任”倾向的具体内容。正如盛洪所说,“自由放任”的深层含义是“遵从自然的秩序,遵从自然秩序演化出来的结果”【13】。遵从自然秩序,遵从自然秩序的演化结果,必然意味着要尊重个体追求物质财富的努力,尊重因个体差异而产生的劳动分工,保障自由贸易,减少政府的干预。这些正是现代“自由放任主义”的基本内容。本文即从这几个方面切入,详细考察儒家经济思想的“自由放任”倾向。基于篇幅限制,本文的考察范围主要限制在先秦时期。
一、儒家式的“经济人”
魁奈认为,“社会的基本法则是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的法则”【14】,人类遵从自然秩序的法则完全是出于自利心的自觉行为,因而每个人在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客观地促进着社会的整体利益。这就是重农学派“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主张的逻辑,这个逻辑实际上也就是后来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儒家一向重视“义利之辨”,自然不是相信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然能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但儒家之所以重视“义利之辨”,也正是基于对个体之自利心的深刻洞察。
首先,儒家承认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的基本情欲。
孔子认为,“人既是精神存在,也是物质存在”【15】。作为物质的存在,人必然有物质上的欲求。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礼记·礼运》)“饮食”是生存需要,“男女”是性的需要,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之大欲。并且,人不仅欲饮食,欲男女,还欲美味,欲美色,欲富贵。所以孔子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人人皆是如此,孔子自己也不例外。
孟子对人之情欲抱持一种批判和改造的态度,但他的批判与改造正建立在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的基本欲望这一前提之上。他说:“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孟子·万章上》)。他批判告子的“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之说,只是反对将人的物质欲求看做本性之固有,以绝人之妄求,而非完全否定人的物质欲求。故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实际上是承认物质欲求亦是性之所有,只是现实中不能必如其愿,故托于命而不谓之性。
荀子的欲求论思想更加丰富【16】,他将物质欲求看做人之本性使然,曰:“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所生而有”者是性,性发而为情,故又曰:“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同上)《荀子·王霸》亦曰:“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綦,训极,或以为“甚”之误17。欲求得不到满足,便会相互争夺而导致混乱,故荀子以人性为恶,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性恶》)荀子的类似表述无法一一赘举,虽然他的最终目的也是要规范人的欲求,即“化性起伪”,但其“化性起伪”的努力仍然是以人的自利心为前提。
其次,儒家认可、甚至鼓励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行为。
既然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的基本情欲,那么便不应对个体追求物质财富的行为一概抹杀。事实上,儒家认可甚至鼓励个体追求物质财富的行为。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其本意并非以义利判别道德意义上的君子小人,而是界定不同身份地位者的经济伦理——至少两汉的儒家学者都是这样理解【18】,肯定一般民众的职分就是追求物质财富。在孔子那个时代,人们并不讳言利,也不羞于求利。孔子自己也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向来儒者多强调富贵的“不可求”,但孔子首先说的是富贵“可求”的情形,如果富贵可求,即便是为人执鞭驾车的贱役他也可以去做。孔子确曾做过委吏、乘田这样的小吏,虽然并没有因此而致富。孔子自己虽然没有致富,但他十分器重的弟子子贡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19】。
不仅庶民阶层可以积极地追求自己的物质财富,士大夫亦可以禄致富。孟子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耕者力田,仕者食禄。故周室班爵禄,虽诸侯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必使“禄足以代其耕也”(《孟子·万章下》)。先秦时期,士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失其位则失其禄,也就失去了生活来源。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孟子·滕文公下》)对于士来说,“无君”便没有了工作,也就失去了生活来源,所以“皇皇如也”,亲友皆来慰问。为了生活,不得不努力找工作,所以“出疆必载质”。子张曾“学干禄”(《论语·为政》),三千弟子几人没有干禄之心呢?孔子认为士在治道清明的时代就应该积极入仕,并可以坦然接受由此带来的富贵,曰“邦有道,榖”(《论语·宪问》)。宜于出仕却不出仕,以致于身处贫贱,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论语·尧曰》),说的便是周有天下,大封于宗庙,贤者得禄而富。儒者积极出仕,非为禄廪,但德配其位,材堪其任,得禄而富,未为不可。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颜渊箪食瓢饮,原宪不厌糟糠,皆非恶富贵而好贫贱。
很多人批评儒家强调“义利之辨”,限制了人们的物质欲求,但儒家却认为礼义这一套渊源自先王的自然法则,恰恰是成全人们的物质欲求的。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以起也。”(《荀子·礼论》)荀子还严厉批评了当时的“去欲论”和“寡欲论”,曰:“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荀子·正名》)他认为人的欲望不可能消灭,也不可能减少,虽然欲望不一定皆能得到满足,但有欲望并想办法去实现欲望是人性之本然,是人之常情。“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同上)所以,即使要防止个体求利行为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是去消灭或压制人们的欲望,而是应该以道、以礼义去引导人们的追求物质财富的行为,以使每个人的欲望都能得到更好的满足。
所以,儒家政治以富民为首务,而富民就是任民自富。
物质财富是人的根本欲求,所以,满足人们的欲求,实现人民富裕是儒家政治的第一要务。《周易·系辞下》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故《尚书·洪范》箕子陈八政,食、货为先。孔子进一步提出了“求富”思想,认为“富民、足民是为政、治国的基本要求”【20】。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然后“教之”(《论语·子路》)。“富民之论,不但为孔子经济学说之基础,亦为儒家主张之一大特点”【21】。孟子发扬儒家的富民思想,认为使民“养生丧死无憾”是“王道之始也”,曰“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主张明君必“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论“富国”,以“富民”为基础,认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富国》)。
但是,儒家之“富民”绝不是通过国家力量直接为人民分配财富,而是主张采取放任的政策,让每个人自己去实现自己的利益。孔子曰:君子为政,“惠而不费”。“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这个“惠”字,与子谓子产“其养民也惠”(《论语·公冶长》)的“惠”字同义,皆是“爱利”的意思【22】。所谓“惠”,就是指政府应施爱利于民。政府爱利人民是“惠”,但又要“不费”,“不费”就是不必耗费公帑以富民。政府做到“不费”的途径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之所以能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正意味着“民”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且正在自觉地追求着自己的利益。政府的“因”就是要顺应人们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放任人们自己去实现自己的利益。在这个“因”的过程中,政府所应该做的,只是协调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为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行为提供便利。如此,则政府有施惠之名,却无耗费之实。所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就是儒家式“经济人”假设的最好表达形式。
二、儒家的劳动分工思想
亚当·斯密认为,引起劳动分工的原因是人性中那种“互通有无、进行物物交换、彼此交易的倾向”【23】,而不是不同的人存在着天赋才能的差异。所谓人性中的那种“互通有无、进行物物交换、彼此交易的倾向”,实际上就是个体源于自利心的多样化欲求。但劳动分工之成为必要,即使不是因为个体天赋才能的差异,也是由于个体天赋才能的局限性,即由于个体满足自己多样化欲求之能力的局限性,因而不得不进行分工合作。儒家对劳动分工带来的经济效益有清楚的认识,因而充分尊重这种自然秩序演化的结果。
(一)君子与小人——脑力劳动亦创造价值
君子和小人,在先秦的很多语境中分别指贵族统治者和一般民众。贵族统治者主要从事脑力劳动,一般民众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儒家十分重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认为脑力劳动也同样创造价值。
如前所述,孔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实质上强调的便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他一再告诫“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即谓作为脑力劳动者的君子,应该用心力于布道教化,专心做好社会治理工作,为体力劳动阶级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而不是自己亲自去从事生产劳动。所以,当樊迟请学稼为圃时,孔子不仅推托“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还批评他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孔子并非否定农业生产活动之价值,只是他开创私学实欲培养治国平天下的君子。社会上不缺少能够为稼为圃的体力劳动者,真正缺少的是能够治理国家天下,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保障劳动阶层安居乐业的君子。如果君子好仁好礼好义好信,将国家治理好,则天下的劳动者自会“襁负其子而至矣”,又何必亲自从事体力劳动呢?他创造的社会价值又岂是收获多少粮食可以衡量的呢?
荷蓧丈人批评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语·微子》),实际上是对脑力劳动的歧视。农家学派也认为“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飱而治”(《孟子·滕文公上》),抹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别,抹杀脑力劳动的价值。孟子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批评他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同上)在孟子看来,不仅物质生产部门内部不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物质生产部门和精神生产部门之间,即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如果没有脑力劳动者对社会的有效管理,不能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体力劳动者就无法安定地生产和生活。在这次辩论中,孟子代表儒家,“充分肯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社会分工”【24】。彭更也疑惑“士无事而食”,孟子再次强调了脑力劳动的社会价值,认为脑力劳动者绝对不是不劳而获,坐吃白食,而是在创造着人类社会健康运转所不必不可少的精神财富,曰:“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孟子认为应该“食功”而不是“食志”(《孟子·滕文公下》)。
(二)士、农、工、商——不同分工共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孟子和农家学者的辩论,不仅强调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意义,还强调了不同体力劳动者之间分工的重要意义,就连农家学者最后也不得不承认“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孟子·滕文公上》)。在孟子看来,劳动分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不断地丰富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如果没有劳动分工,人类社会恐怕还停留在茹毛饮血的原始阶段。故曰:“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同上)
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劳动分工的思想,对劳动分工的社会意义阐述最为详细。他说:“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荀子·富国》)为了避免社会的“穷”和“争”,“则莫若明分使群矣”。“明分”有制定“度量分界”的意思,所以人们一般将“明分”看做荀子的分配思想,但实际上它也包含着劳动分工意思。“明分”就是明个人的职分,农夫众庶,将率百官,圣君贤相,各有其职分。人人各明其分,各尽其职,天下才能富足。故曰:“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同上)人人各明其分,各尽其职,则天子可以垂拱而治。职分既明,“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荀子·王霸》)。荀子将“农农、士士、工工、商商”等劳动分工体系,看做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等伦理等级体系及“贵贱、杀生、与夺”等奖惩体系相辅相成的天下“大本”(《荀子·王制》),认为它们是共同维持社会运转和发展的基本秩序。荀子对劳动分工之社会意义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助于“使人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提高社会生产力;二是促进专业化,有助于改进生产技能,提高产品质量;三是有助于“消除人们之间在物质利益方面的争夺”【25】。
不同劳动皆创造价值,共同推动着社会经济发展。孟子与农家学者辩论的重点便是阐明这个道理。《周礼·考工记》亦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整个社会由六个劳动部门组成,体力劳动部门不仅包括农、工、商的劳动,也包括女性的劳动,与王公、士大夫的脑力劳动一样,都是社会价值创造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维系着社会的运转和发展。《周礼》由战国儒家杂取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制度编撰而成,但作者的目的不是为了汇编史料,而是要设计一套理想的制度,所以它实际上反映了战国儒家的政治社会思想【26】。
(三)因民自利——放任人们自由地选择生产经营活动
陈焕章已经指出,根据孔门的经济理论,人们普遍享有迁移的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享有选择生产经营活动的自由【27】。这正反映了儒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经济管理原则,打破了管仲“四民分业定居”的静态理论。
儒家推动人们的地域流动。在儒家思想中,能否招徕四方的人民是检验政治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孔子认为君子好礼义而讲诚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不必亲自从事生产劳动。因为招徕四方之民,可以发展本国的生产。《礼记·中庸》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七曰“来百工也”,八曰“柔远人也”,“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说的便是招徕他国工人、商旅和劳动力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到了孟子的时代,人民的迁徙似乎已经相当自由,故孟子曰:“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国君“发政施仁”之所以可以吸引到四方的人才,当然是建立在人民能够自由迁徙的前提之上。《穀梁传》曰:“其曰王者,民之所归往也。”(《庄公三年》)儒家倡导王道政治,王道政治就是放任人民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自由地选择仁义之君,自由地选择自己从事生产和生活的地域。
儒家还认可人们自由地选择职业。到了战国时期,劳动阶级不同职业间的流动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了。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然职业不同,其所利者亦不同,“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孟子·公孙丑上》)。能够“不可不慎”,意味着个体应该慎重地选择职业,也意味着个体可以选择职业。陈焕章说:“根据孔教徒的理论,人人均应享有选择其职业的自由,而自由选择职业在古代已是确凿的事实。”【27】此论虽不免夸大其辞,但说自由选择职业是儒家的基本思想倾向,则无不妥。荀子曰:“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荀子·荣辱》)“注错”即措置之义,此处指人的选择。又曰:“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荀子·儒效》)虽然职业皆由学习积累而来,而除了习惯与环境的影响,学不学则在自我的选择,选择的根据完全在于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考虑,确实已经没有强制继承的意味在其中了。
人们从事什么样的生产经营活动,在何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政府不应随意干涉。《礼记·礼运》曰:“故圣王所以顺,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郑玄注:“山者利其禽兽,渚者利其鱼盐,中原利其五谷,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劳敝之也。民失其业则穷,穷则滥。”疏云:“故圣人随而安之,不夺宿习,不使居山之人居川也,不使渚者居中原”,“必各保其业,故恒丰而不敝困也”【28】。强调的便是政府不得干预人们因居住环境不同而选择的生产活动。既然政府不能强迫居山狩猎者去以舟楫渡人为业,不能强迫居渚贩卖鱼盐者去务农耕稼为业,当然也不能强迫农人去从事陶冶,不能强迫工人去从事贸易,不能强迫商人去从事农耕,而应放任人们去从事自己认为最有利的职业和工作。这也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应有之义,邢昺曰:“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兽,渚者利其鱼盐,中原利其五谷。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则是惠爱利民在政,且不费于财也。”【29】邢昺的解释,概括言之,就是遵守自然法则,顺应因自然差异而产生的分工。
三、儒家的自由贸易思想
劳动分工意味着生产专门化,意味着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个体的多方面欲求可以得到更好地满足,但同时也意味着一个人无法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产品生存下去,因而不能独占自己的劳动产品,必须用自己生产的剩余产品去交换他人生产的剩余产品,于是贸易成为必然。“自由放任主义”主张自由贸易,即取消对贸易的任何阻碍,推动商品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自由流通。自由贸易有利于优势互补,儒家对优势互补原理尚无清楚认识,但对贸易带来的物质生活的丰富却有深刻的体验,因而坚决地主张自由贸易,反对征收商税。
(一)不抑商,鼓励商品贸易的发展
儒家重农但不抑商【30】,儒家文献中多有鼓励商品贸易的记载。《尚书·益稷》曰:“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说的是禹治水时,后稷教民耕种,并鼓励人们交易有无,解决了生存问题。《尚书·洪范》八政“二曰货”,其中也包含着发展商品贸易的内容。周公告诫康叔:“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诰》)就是鼓励民众在农闲时去远方贸易。西周之末,郑国与商人共同开拓新疆土,并订立了世代相守的盟约。子产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左传·昭公十六年》)又葵丘之盟,曰“无遏籴”(《孟子·告子下》),规定各国不能阻碍粮食贸易。公元前562年,郑与晋、宋等盟,曰“毋蕰年,毋壅利”(《左传·襄公十一年》),规定各国不能阻碍粮食贸易和商品流通。
孔子对商品贸易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后儒狃于重义轻利的成见,认为这是孔子在批评子贡。但实际上这句话中的“命”当如王弼之说,释为“爵命”,即殷仲堪所谓“不受矫君命”,江熙所谓“赐不荣浊世之禄”【31】。子贡曾仕于鲁、卫,盖见道之不行,乃“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32】,在孔门中最为富有(《史记·货殖列传》)。孔子也曾以商贾自况积极入世的心情,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叶公问政,孔子曰:“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礼记·中庸》曰:“柔远人。”所谓“远者”“远人”,指的便是四方商旅。
孟子的贸易思想反映在他的分工理论中。当他指出劳动分工的必要性时,也揭示了贸易的必要性。孟子认为没有分工便没有生产的进步,但如果没有贸易,个体的物质生活需求仍不能得到多方面的满足。并且,孟子还认为不同分工之间的贸易是平等互利的关系,不存在一方损害另一方的问题。他说:“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连续的提问,逼得陈相也不得不承认:“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孟子·滕文公上》)因为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因为贸易,使每个人都可以享用其他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否则,只有分工没有贸易,每个人就只能消费自己的产品,而无法消费他人的劳动产品,每个劳动者的剩余产品就只能浪费掉。所以,孟子责备彭更说:“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孟子·滕文公下》)
荀子说“工商众则国贫”,要求“省商贾之数”(《荀子·富国》),但他的目的不是要限制商品贸易的发展,而是出于工、商业的发展必须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考虑。荀子高度赞赏商品贸易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极大丰富,曰:“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荀子·王制》)四海之间相距千万里,其物产中国皆得而用之,正有赖于贸易的发达。泽人不伐木,山人不网鱼,农夫不制器,工贾不耕种,而皆能通其用,亦是赖于贸易的发展。
(二)反商税,主张减少对商品流通的阻碍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可能已开始对商品征收关税和市场管理税、仓储税。《周礼·司徒》曰:“廛人掌敛市布、布、质布、罚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布,是“列肆之税布”;布,是“无肆立持者之税也”,或认为是“守斗斛铨衡者之税也”;质布,是“质人之所罚犯质剂者之泉也”;罚布,是“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是“货贿诸物邸舍之税”【33】。又司关“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国凶札,则无关门之征,犹几”。“几”通讥,是检查之义。司关不仅负责征收过往商品的关税,还负责征收储存于关下之货物的仓储税,只有在遇到饥荒或疾疫的年份才免征关税,但仍然例行检查。
征税必然会阻碍商品贸易的发展,《周礼》的作者编列了这些官职,表示他认同这些税收,但儒家主要学者都明确反对征收商税的行为,尤其反对征收关税的行为。反对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儒家认识到商品贸易可以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而征收商税,尤其征收关税,会限制商品贸易的发展;二是儒家有“柔远人”“远者来”的政治理想,而征收关税会阻碍其招商引资——招徕人力资本的政策。所以,鲁大夫臧文仲“置六关”【34】以征商旅之税,而孔子责其“不仁”(《孔子家语·颜回》)。
孟子不仅反对征收关税,还反对征收市场管理税、仓储税。他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孟子·公孙丑上》)按郑众的解释,“廛”是“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货物者也”,即储存商品货物的仓库。所谓“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就是“货物贮藏于市中而不租税也”,“其有货物久滞于廛而不售者,官以法为居取之”【35】。“讥”是检查过往客商携带的货物,看是否有违禁物品。有违禁物品当然要查收,但不应该对合法货物征收关税。《礼记·王制》亦曰“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很可能与孟子的思想存在继承关系。孟子批评战国诸侯置关以征税的行为,曰:“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孟子·尽心下》)古之关卡,唯检查违禁物品,主要职责是保护过往商旅安全,而战国诸侯因兼并战争的开支,不仅对农民征收各种赋税,还设重重关卡对过往商旅征收重税,其所以为暴也。
荀子也主张政府应该促进商品贸易的发展,免征关税。曰:“关市几而不征,……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荀子·王制》)又曰:“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荀子·王霸》)荀子认为“平关市之征”是“国富”和“以政裕民”的重要措施。“平”是除去的意思,批评战国诸侯“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荀子·富国》)。
(三)反干扰,保护正常的市场竞争活动
儒家似乎已经认识到市场机制影响商品价格的规律,因而认为商品有贵贱是市场竞争的正常表现。孔子和子贡曾经讨论过玉和珉的价格问题,君子“贵玉而贱珉”,子贡倾向于认为是玉少而珉多的原因,即供求关系决定的;孔子则认为是由于二者使用价值的差异,即二者带给消费者的效用不同,曰:“夫玉者,君子比德焉”(《荀子·法行》)。无论供求关系,还是商品使用价值的高低,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市场机制运行的规律。
孟子与农家学者的辩论也涉及到市场定价的问题。农家学者主张以“数量”为标准规定商品价格,曰:“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孟子·滕文公上》)但即使同类商品在数量上相当,它们在质量上也会存在美恶精粗的差异,能带给人们的效用不同,生产者付出的劳动也不同。如果按农家的主张,生产者只有降低质量才能获得利润,最终必然导致市场上的商品皆粗恶不堪。所以孟子坚决反对农家的主张,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同上)张守军认为“情”即“实”,与“名”相对,“名是形式,是表面的东西,实则是内在的东西;名是表现实的,实对名则有决定的作用”。因而孟子所谓的“物之情”,“就只可能是隐藏在商品价格的背后并成为决定价格的基础的商品价值”【36】。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商品的价值问题,只是孟子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价值的实体是什么。
孟子还提出了反“龙断”(垄断)的问题。他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孟子·公孙丑下》)在孟子看来,“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是贸易的基本精神,对于这种正当的贸易活动,政府只需管理而不需征税。但是,当有人试图操控市场,居积投机,追求暴利时,政府就应该通过征收商税的形式予以惩戒。“龙断”本义是“冈垄断而高者”【37】,孟子用以指市场中的高亢之地,商人登而以便了解整个市场行情,从而操控市场,以获取暴利。当时的“龙断”主要指市场投机行为,远远没有今天的垄断那么严重,但它对正常的市场竞争仍然会产生破坏作用。
四、儒家式的“小政府”
放任人们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必然意味着减少政府的干预。“自由放任主义”认为政府管的越少越好——管的少的政府就是“小政府”。儒家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实际上也是强调政府不应该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追求的正是一种“小政府”的模式。在社会层面,“小共体本位”是儒家抵御“大政府”的有力武器【38】;而在经济层面,儒家则通过限制政府的收入与开支,从而客观上约束了政府权力和规模扩张。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为政者和政府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为政者的行为往往就是政府的行为,所以我们下面讨论政府的行为时,自然也包括了为政者的行为。
首先,以义为利,反对政府通过任何手段与民争利。
儒家绝对反对政府通过行政权力掠夺人民财富。周厉王使荣夷公专利,芮良夫谏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国语·周语上》)厉王不听芮良夫的建议,最终被国人流放于彘。《国语》被称为《春秋》外传,芮良夫的这段话也成为后世儒家反对政府与民争利的经典依据。周幽王重蹈覆辙,《诗》云:“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如贾三倍,君子是识。”(《诗经·大雅·瞻卬》)幽王夺民之土田子女,争商贾之利,最终被犬戎杀于骊山。至周景王,废轻钱而铸大钱,等于将人民的积蓄归零,其实质也是掠夺人民的财富。故单穆公强烈反对,曰:“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国语·周语下》)人民失去财富,将会流徙他方。《周易·解卦》六三曰:“负且乘,致寇至。”即谓为政者舍仁义而逐于财利,必招致寇盗祸患。
儒家也坚决反对政府直接从事生产或经营活动以与民争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要求“位居社会上层的官员与士人,伦理活动先于理财活动”【39】。臧文仲使“妾织蒲”(《孔子家语·颜回》),孔子批评他不仁。《礼记·大学》引孟献子之言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蓄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即谓有禄廪者不得蓄养鸡豚牛羊,有采邑者不得加征租税。加征租税等于直接掠夺人民的劳动成果,而使妾织蒲,蓄养鸡豚牛羊,无论是送到市场上销售还是留作自用,都是与民争利。因为体力劳动者通过向脑力劳动者出售剩余产品以获得收入,如果脑力劳动者也从事生产或经营活动,必然会影响到体力劳动者剩余产品的销售,也就等于将他们应得的收入夺走了一部分。故《礼记·大学》又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政府直接从事生活经营活动,将使劳动者在竞争中陷于极不利的地位。董仲舒曰:天亦有所分予,人不能竭利而取,故“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如果为政者“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则人民完全无法与之竞争,“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穷”,必然导致“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产生动乱。“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公仪休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40】
其次,主张什一之税,反对政府随意加征赋税。
儒家主张轻赋薄敛,反对对土地产品以外的任何物品征税。孔子曰:“时使薄赋,所以劝百姓也。”(《礼记·中庸》)使民以时,轻赋薄敛,可以激励劳动者致力于生产活动。孟子亦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孔子所谓“薄赋”,孟子所谓“薄其税敛”,皆是指土地产品税。儒家主张实行单一的土地产品税,反对对土地产品税之外的任何其它物品征税。上文已讨论过儒家反对征收商税,如孟子所谓“市廛而不征”,“关讥而不征”,除此之外,孟子又说“廛无夫里之布”(《孟子·公孙丑上》),即还反对征收房产税。荀子发展了儒家轻赋薄敛的思想,曰:“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荀子·王制》)荀子主张只对土地产品征收什一之税,除此之外,不仅不征关税,也不征自然资源税。荀子还认为轻赋薄敛可以裕民富国,曰:“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荀子·富国》)
儒家理想的税收制度是建立在“彻”法或“助”法上的什一税制。鲁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论语·颜渊》)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孟子·滕文公上》)“贡”法是取若干年之平均产量为一固定税额,不考虑年成好坏皆以此税额征税;“助”法是井田制下的税收制度,以公田上的收入作为税收;“彻”法是根据每年的具体产量确定当年的税额,随年成好坏而有所增减。虽然三种税收制度名义上都是十分之一的税率,但“贡”法有丰年寡取、凶年多取之弊;“彻”法年年检校,不仅浪费行政资源,还存在着检校官吏舞弊的风险;唯“助法”公田私田分明,公私收入同随年成好坏增减,又无官吏舞弊之风险。所以,三者之中,“贡”法最差,“助”法最优——这正是两千多年来儒家念念不忘“复井田”的重要原因之一。孟子主张“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同上),荀子亦主张“田野什一”(《荀子·王制》)。《公羊传》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宣公十五年》)
在古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加征赋税会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孔子过泰山侧,曾有“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之叹。故儒家十分反对随意加征赋税的行为。冉求帮助季氏加征租税,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礼记·大学》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务财用”即务于增加财政收入,要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加征赋税,儒家认为这是小人之政。《鲁诗》曰:“履亩税而《硕鼠》作。”【41】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即不废公田,“又履其余亩,复十收其一”【42】,由原来的十税一变成了十税二,故《春秋》三传都严厉地批评这件事情。《左传》曰:“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宣公十五年》)《穀梁传》曰:“初税亩,非正也。”“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宣公十五年》)“悉”谓竭尽民力。《公羊传》则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宣公十五年》)孟子亦有“大桀小桀”“大貉小貉”的批评,并曰:“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孟子·告子下》)荀子也批评战国诸侯:“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荀子·富国》)
儒家主张轻赋薄敛,反对与民争利,反映了其“藏富于民”的思想。唐庆增说,儒家的“自由放任主义”就是“藏富于民”【43】。鲁哀公欲加税,有若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藏富于民”是儒家“富民”政治的必然结果,它要求限制政府在劳动产品再分配中的份额,进而限制政府的开支,即荀子所谓的“节其流”(《荀子·富国》)。
再次,量入为出,限制政府的开支和规模。
为了限制政府开支,儒家主张“量入为出”的预算政策,反对政府的任何浪费行为。“量入为出”就是根据赋税收入决定开支和用度,而不是根据开支和用度征收赋税。《礼记·王制》曰:“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冢宰每年在赋税征收完成以后做来年的财政预算,每年的收入在留出一部分积蓄之后才是下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冢宰根据年成的丰歉和可支配收入的多少预算下一年的支出。“祭用数之仂”,“丰年不奢,凶年不俭”。除祭祀外,丰年“多不过礼”,歉年“少有所杀”【44】。
在有限的预算下,政府必须节俭开支。故有土之君,除了在礼乐制度和丧葬祭祀事宜上不能节俭以外,“即安其居,节丑其衣服,卑其宫室,车不雕几,器不刻镂,食不贰味,以与民同利”(《礼记·哀公问》)。禹就是一个这样俭奢得当的典范,孔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禹俭约自身而能够用心于祭祀,致力于礼乐制度和发展生产,所以孔子对他无所非议。不仅君主,对士大夫也有同样的要求。《礼记·王制》曰:“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庶羞不逾牲,燕衣不逾祭服,寝不逾庙。”“故”者,祭、飨之事。如非祭祀或飨宾客,诸侯不得杀牛,大夫不得杀羊,士不得杀犬、豕,庶人不得食卵、鱼、豚、雁,平常饮食不能过于祭祀之牺牲,衣服不能过于祭服,室屋不能过于宗庙。政府的消费应该在“时”与“礼”的规范之下,孟子曰:“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上》)赵岐曰:“食取其征赋以时,用之以常礼,不逾礼以费财也,故蓄积有余,财不可胜用也。”【45】不过在这一点上,荀子与孔孟存在分歧,把君主奢华享受作为维护其等级地位的标识。
基于“量入为出”的预算政策,儒家主张限制政府规模,反对人浮于事,机构膨胀。荀子曰:“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重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荀子·富国》)主张减少士大夫的数量以节省开支用度。张劲涛认为,荀子使用“节流”一词的含义,就是“节约财政开支”,不仅限制统治阶层的奢侈消费,“还有个节约政府机构的行政经费的问题”【46】。
结语
综上所述,儒家承认追求物质财富是每个人的基本欲望,荀子甚至认为这种欲望源自人的本性,因而认可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行为,高度肯定基于个体能力限制及为了满足多方面欲求而产生的劳动分工,认为不同分工共同促进着社会经济发展,放任人们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和经济活动,主张推动商品贸易,反对阻碍商品贸易的任何税收,反对扰乱市场竞争的干预政策和垄断活动,反对政府通过行政权力或直接从事经营活动与民争利,主张轻赋薄敛,限制政府开支和政府规模等,都清晰地展现出儒家经济思想的“自由放任”倾向。陈焕章说,历史上“中国人享有太多的理财自由,除去少数因社会的缘故而限制消费的法律外,民众确实在做他们想做的事”,即使那少数限制消费的法律,很大程度上也形同虚设,“是风俗支配中国的商业社会,而非法律”【47】。风俗支配中国古代的商业社会,而儒家思想支配中国古代的风俗。儒家思想不仅支配风俗,还支配着中国古代的法律和政治。历史上中国人享有的经济活动自由,虽然有政府行政能力不足的原因,但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在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倾向,也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儒家经济思想和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儒家并没有将“自由放任”作为全部经济活动的价值追求,儒家虽然承认人们自利心的存在,并认可个体追求物质财富的行为,但显然并不相信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然会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因而主张以礼义规范和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特别强调义利之辨。儒家反对政府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不适当的干预,但儒家从来没有否定政府在制度建设、保障和推动经济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正如陈焕章所说,儒家既有主张“自由放任”的一面,又有主张社会立法的一面,儒家主张政府立法管理和监督经济活动,主张政府公平地分配生产资料,保护人民的财产,进行社会产品的再分配,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等。儒家是在国家治理的整体框架下思考经济问题的,首先考虑的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平的问题。单纯的“自由放任”政策并不必然能实现这些结果,所以儒家一直努力追求“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之间的动态平衡。在实际的经济发展中,到底应该是“自由放任”多一点还是国家干预多一定,没有一个固定的界限,而应根据当时的社会问题和实际需要调整政策。但无论何种情况,两种政策必须保持相对的平衡。不然,要么导致国家力量不足,要么导致社会贫困,最终加剧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